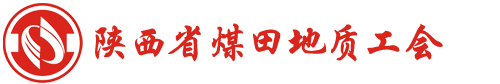女工天地
童真岁月
浏览量:928
作者:王晓梅
来源:
日期: 2015-07-07
农村的孩子伴随着泥土长大,这种泥土气息融入到血液里,渗透到骨髓中,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总有一根绳子拉着我们,割舍不掉。——题记
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农村的水土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在我身上始终割舍不掉那种气息。即使离开农村走入城市多年,我依旧怀念那段童真岁月。
和村里的大多数同龄孩子相比,我是幸福的,甚至是“有钱人”。我可以奢侈地吃上北冰洋、黑旋风,可以每周吃一顿荤菜,可以向小伙伴展示爸爸从城里带回的小玩意儿,因为爸爸是工人,这在当时的农村可以用“小资”来形容。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至今老家还有一台老式收音机,我们几个小孩儿围着收音机学人家唱歌,“打扮打扮不要怕花钱,耳环项链,样样都齐全。”不懂歌词意思,就那样唱出来,在一旁淘麦(洗小麦磨面)的妈妈听了笑得合不拢嘴:“你知道这歌词什么意思吗?你就唱啊!”“不知道!”我回答得理直气壮,小嘴嘟得老高。妈妈任由我唱,高兴的时候还会给我打拍子,我则手舞足蹈地边唱边跳, 至于跳的什么我也不知道,甚至有时候会“惊动”邻居。
那时候家家都住窑洞,一家挨着一家,邻里之间笑眯眯,扛着锄头,互道一声:“上地啊!”“下地啊!”简单、淳朴、真实。伴随着鸡的打鸣,狗的汪汪,日出而起,日落而息,农村的生活简单得就像一条直线,没有弯曲,笔直地延伸到天尽头。
最喜欢夏天,和小伙伴们吆三喝四的去放羊,羊儿吃得高兴,我们玩得欢快,跳皮筋、抓石子、跳绳、爬树、踢房子、玩弹弓、拍画片,一起趴在地上看蚂蚁搬家,一起躲在草里抓蛐蛐,一起脱了衣服扑蝴蝶,回家个个灰头土脸。晚上,我们会去抓知了,那时候的知了真多,树上、地里都是知了,抓的人也多,还有人抓蜈蚣、蝎子去卖钱,当然我们这些孩子只抓知了。一大帮人,浩浩荡荡,从村西头跑到村东头,一人一个小手电,明晃晃的,满载而归。第二天一早,油炸知了的香味就弥散了整个村子。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大肉只有过年或重大节日的时候才可以吃得到,而知了则是整个夏天的美味。
在农村,每年都有集市,每个村子的集市时间不同,内容却也大同小异。集市那天,各种小商小贩齐聚村子,各种小吃、零用物品齐备,我们那里有石头会、西瓜会和腊月会,这些是我们小孩儿最期盼的,因为这一天,家里会来很多亲戚,会很热闹,也会有很多好吃的。每当这个时候的头天晚上,我就会激动到睡不着觉,第二天天一亮,就直奔集市转几个来回,身上揣着妈妈给的毛票,像宝贝一样捂着,小心地拿出毛票,买一把粘牙糖、一对塑料耳坠,粘牙糖拉出长长的丝,开心地向妈妈展示自己“淘”到的宝贝。现在我依旧怀念那种感觉,可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我那样怦然心动。是自己长大了,还是离开农村太久了?最喜欢腊月会,因为腊月会完了就过年了,也只有过年大人才允许我们“大吃大喝”。说是“大吃大喝”,其实也是有计划的吃喝,不能放开的吃,因为农村人重亲戚,每年的走亲戚也会走到初十,甚至十五之后,在这期间家里必须留够充足的食材,以备亲戚来了有得做。
也只有这样的日子,我们才有福利看到露天胶片电影,没有爆米花,没有空调,没有立体音响,没有舒适的座椅,一台胶片机,一张白布,被风吹得呼啦啦响,声音随着风向忽大忽小,可我们的身板依旧挺得笔直,认真地观看,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镜头,甚至忘了嬉闹。因为在当时的农村,看电影时极其奢侈的事儿,连露天电影也是不常有的,村里的男女老少聚在一起,也是为了一年不多的几次露天电影。
农村的生活,简单、直接,从这一头可以看见另一头。外婆跟我们住得很近,一个村东一个村西,中间只隔几户人家,从我们家可以看到外婆家的烟囱,每当烟囱冒烟,我就知道外婆在向我招手,喊我吃饭。妈妈说我“赖”,外婆也说我“赖”,不过我知道那是宠溺的说。我会端着碗边走边吃,一直吃到外婆家,再从外婆家锅里盛出我喜欢吃的饭,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喜欢吃外婆家的饭胜过我们家里的。外婆做饭我拉火,槐花饭、灰灰饭、麻团,各种野菜饭,在灶火里埋几颗红薯、土豆、茄子,整个院子混合着各种饭香,外婆满脸笑意。外婆家的院子很大,大得可以养成群的鸡,还有一头猪、一头牛,小鸡围着外婆咯咯地叫,我围着鸡窝转,小心地从鸡窝里掏出还带有小鸡体温的蛋,如获至宝般地放在外婆的篮子里,外婆的小脚跑得又快又准。放学回家,我总会先绕到外婆家,我喜欢外婆喊我馋猫,喜欢外婆给我书包里塞满各种好吃的,喜欢翻外婆的“百宝箱”,即使什么宝贝都没有,即使翻过很多遍,我依旧乐此不疲,一件件地拿出来再一件件地放回去,这是一种习惯,亦是一种想念。
后来,我上初中去了镇里,每个周末回来一次,每个周末见一次小伙伴,见一次外婆。再后来,到了高中,去了县里,离家更远了,一周变为一月,但我仍执拗地相信,我会回去。妈妈说那里是你的根,你的养分都在那里。最后,上了大学,去了省会城市,一月变为一年,甚至更久。直到现在上了班,在城市里扎了根、发了芽,有了爱人、有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家。童年的玩伴,童年的道路,童年的记忆都愈加模糊,就像村口的涝池,被圈在原地,水愈来愈少,最后被填埋,建起了一排排平房。
有人说,一个人的记忆就是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
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农村的水土伴随了我整个童年,在我身上始终割舍不掉那种气息。即使离开农村走入城市多年,我依旧怀念那段童真岁月。
和村里的大多数同龄孩子相比,我是幸福的,甚至是“有钱人”。我可以奢侈地吃上北冰洋、黑旋风,可以每周吃一顿荤菜,可以向小伙伴展示爸爸从城里带回的小玩意儿,因为爸爸是工人,这在当时的农村可以用“小资”来形容。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至今老家还有一台老式收音机,我们几个小孩儿围着收音机学人家唱歌,“打扮打扮不要怕花钱,耳环项链,样样都齐全。”不懂歌词意思,就那样唱出来,在一旁淘麦(洗小麦磨面)的妈妈听了笑得合不拢嘴:“你知道这歌词什么意思吗?你就唱啊!”“不知道!”我回答得理直气壮,小嘴嘟得老高。妈妈任由我唱,高兴的时候还会给我打拍子,我则手舞足蹈地边唱边跳, 至于跳的什么我也不知道,甚至有时候会“惊动”邻居。
那时候家家都住窑洞,一家挨着一家,邻里之间笑眯眯,扛着锄头,互道一声:“上地啊!”“下地啊!”简单、淳朴、真实。伴随着鸡的打鸣,狗的汪汪,日出而起,日落而息,农村的生活简单得就像一条直线,没有弯曲,笔直地延伸到天尽头。
最喜欢夏天,和小伙伴们吆三喝四的去放羊,羊儿吃得高兴,我们玩得欢快,跳皮筋、抓石子、跳绳、爬树、踢房子、玩弹弓、拍画片,一起趴在地上看蚂蚁搬家,一起躲在草里抓蛐蛐,一起脱了衣服扑蝴蝶,回家个个灰头土脸。晚上,我们会去抓知了,那时候的知了真多,树上、地里都是知了,抓的人也多,还有人抓蜈蚣、蝎子去卖钱,当然我们这些孩子只抓知了。一大帮人,浩浩荡荡,从村西头跑到村东头,一人一个小手电,明晃晃的,满载而归。第二天一早,油炸知了的香味就弥散了整个村子。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大肉只有过年或重大节日的时候才可以吃得到,而知了则是整个夏天的美味。
在农村,每年都有集市,每个村子的集市时间不同,内容却也大同小异。集市那天,各种小商小贩齐聚村子,各种小吃、零用物品齐备,我们那里有石头会、西瓜会和腊月会,这些是我们小孩儿最期盼的,因为这一天,家里会来很多亲戚,会很热闹,也会有很多好吃的。每当这个时候的头天晚上,我就会激动到睡不着觉,第二天天一亮,就直奔集市转几个来回,身上揣着妈妈给的毛票,像宝贝一样捂着,小心地拿出毛票,买一把粘牙糖、一对塑料耳坠,粘牙糖拉出长长的丝,开心地向妈妈展示自己“淘”到的宝贝。现在我依旧怀念那种感觉,可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我那样怦然心动。是自己长大了,还是离开农村太久了?最喜欢腊月会,因为腊月会完了就过年了,也只有过年大人才允许我们“大吃大喝”。说是“大吃大喝”,其实也是有计划的吃喝,不能放开的吃,因为农村人重亲戚,每年的走亲戚也会走到初十,甚至十五之后,在这期间家里必须留够充足的食材,以备亲戚来了有得做。
也只有这样的日子,我们才有福利看到露天胶片电影,没有爆米花,没有空调,没有立体音响,没有舒适的座椅,一台胶片机,一张白布,被风吹得呼啦啦响,声音随着风向忽大忽小,可我们的身板依旧挺得笔直,认真地观看,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镜头,甚至忘了嬉闹。因为在当时的农村,看电影时极其奢侈的事儿,连露天电影也是不常有的,村里的男女老少聚在一起,也是为了一年不多的几次露天电影。
农村的生活,简单、直接,从这一头可以看见另一头。外婆跟我们住得很近,一个村东一个村西,中间只隔几户人家,从我们家可以看到外婆家的烟囱,每当烟囱冒烟,我就知道外婆在向我招手,喊我吃饭。妈妈说我“赖”,外婆也说我“赖”,不过我知道那是宠溺的说。我会端着碗边走边吃,一直吃到外婆家,再从外婆家锅里盛出我喜欢吃的饭,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喜欢吃外婆家的饭胜过我们家里的。外婆做饭我拉火,槐花饭、灰灰饭、麻团,各种野菜饭,在灶火里埋几颗红薯、土豆、茄子,整个院子混合着各种饭香,外婆满脸笑意。外婆家的院子很大,大得可以养成群的鸡,还有一头猪、一头牛,小鸡围着外婆咯咯地叫,我围着鸡窝转,小心地从鸡窝里掏出还带有小鸡体温的蛋,如获至宝般地放在外婆的篮子里,外婆的小脚跑得又快又准。放学回家,我总会先绕到外婆家,我喜欢外婆喊我馋猫,喜欢外婆给我书包里塞满各种好吃的,喜欢翻外婆的“百宝箱”,即使什么宝贝都没有,即使翻过很多遍,我依旧乐此不疲,一件件地拿出来再一件件地放回去,这是一种习惯,亦是一种想念。
后来,我上初中去了镇里,每个周末回来一次,每个周末见一次小伙伴,见一次外婆。再后来,到了高中,去了县里,离家更远了,一周变为一月,但我仍执拗地相信,我会回去。妈妈说那里是你的根,你的养分都在那里。最后,上了大学,去了省会城市,一月变为一年,甚至更久。直到现在上了班,在城市里扎了根、发了芽,有了爱人、有了孩子、有了自己的家。童年的玩伴,童年的道路,童年的记忆都愈加模糊,就像村口的涝池,被圈在原地,水愈来愈少,最后被填埋,建起了一排排平房。
有人说,一个人的记忆就是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
下一篇:常怀感恩之心,享受健康生活
上一篇:从一名懵懂女孩到二宝母亲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