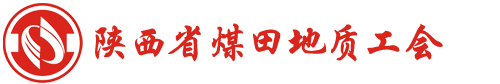那人,那井
5月14日,刘立乾去世的第九天。一间六、七十平方米的单元房里,刘立乾的妻子依然眺望着丈夫工作的地方。这是她多年的习惯。如果不是抬头看到丈夫的遗像,她觉得自己个高身瘦的丈夫,仍然在一个没有人烟的的地方,一脸恬静地守着自己的钻塔或者伸头看着通向“乌金墨玉”的钻井。

同一天,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大院里,钻井工程一公司的32名员工仍然不能相信“领头人”的离开。每次途经刘立乾的窗户时,他们偶然也会驻足半刻然后匆匆离开,伤感依然会涌在心头。
时间回到1982年,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那时还叫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一队。刚进入夏天,这些钻井人突然发现,队伍中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身影,17岁出头的蓝田娃刘立乾来到韩城,接替父亲成了钻井人。之后的38年里,这个蓝田娃就一直闷声打井。这本是一个注定没有彩头的职业,但是刘立乾却打出了名气。他改进了绳索取芯的泥浆配方,大幅节约了泥浆材料费用。他提出了“悬垂防斜技术”,并用三天三夜的时间、N次失败和一次成功,给同行演示了教科书式的钻孔防偏操作流程。在内蒙古上海庙、乌审旗和沙尔陶勒盖等勘探项目中,面对复杂的地层和百米厚的砾岩层,钻井深达千米,刘立乾用了37天完成了第一个深度为915米的钻孔,随后又连续完成两个千米钻孔,为一三一队在内蒙古地区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一三一队准备涉足地热能市场时,刘立乾四处学艺,掌握了地热能钻孔施工的经验和方法并传授给同事。从此,一三一队正儿八经地走进了地热能市场。
在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采访刘立乾时,所有员工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2007年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全国煤炭工业劳模的称号。”人们用同样的开头介绍他。但在结束的时候,都会惋惜地说:“他马上就能退休,可以歇歇了。”话音刚落便是一声长叹。
没有人会想到,2019年春节放假,刘立乾和大家成了永别。刘立乾的蓝田老乡李效益声音深沉地回忆:“他能吃苦、善打硬仗。1983年他去陕北府谷,一去就是十年。冬天的时候,陕北的温度极低,泥浆喷到身上就会结冰,在那一代的钻井人身上,你能看到铁人王进喜的影子。”“他三分之二时间和井在一起。”和刘立乾共事20多年的同事薛启平说,“他不喜欢说话,平时总是俯下身子干活,就像井和钻塔一样,沉默、永不停歇。很多人都知道他带领的4号钻机获‘陕西省青年突击队’称号,他是全国煤炭工业劳模。”

钻井工程一公司的年轻人给刘立乾贴了很多标签。80后的黑云飞觉得刘立乾是个宽厚的人:“爱给我鼓劲,工作上出现问题,他会帮我找问题,并给我破解问题。”90后的赵鹏飞仍然记得,三年前他和刘立乾去渭南地热能项目现场的场景:“那时是夏天,天气很热,工人都趁着午饭时候避避暑,可是放下碗的时候,人们发现刘经理依然在干活。项目用了40天,他就这样干了40天。”而对于32岁的李渊来说,刘立乾让他感到了温情。2015年他和刘立乾曾在府谷工作,“他每次做了好饭都会喊我过来吃,我的帐篷挨着他的帐篷。”后来,李渊兜里没钱的时候,都会去找刘立乾。“他好说话,你哼哼唧唧刚说手里有点紧时,他就把钱包掏出来了。”

刘立乾给同事留下了很多好,但是留给妻子的却是无休无止的痛。在妻子的记忆中,2019年是刻骨铭心的,这是他们最长的厮守。诊断书上的肺部恶性肿瘤揪的她心痛。“再过两年他就退休了,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刘立乾的妻子幻想过很多种退休以后的生活,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命运会用黑色挽结了所有的幻想。
5月5日,刘立乾走了,步履匆匆。他的妻子在文章中说:“四个月与病魔的抗争,是我们厮守最长的日子。我在你驻足的地方总能感觉到你的气味,独守没有你的空房,无尽的黑暗伴随孤独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