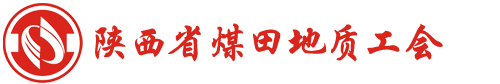罗布泊“7601”——终生难忘的回忆
我以亲身经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为这段“7601”不出世的历史提供惊心动魄的个人视角。1976年6月至9月我参加了代号为“7601”的演习——原子弹实爆条件下部队通过爆心的军事演习,亲身尝试了原子弹爆炸的味道。40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些接触原子弹爆炸的亲身感受和体会,有心提醒大家核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但由于受保密要求的制约,一直未能如愿。鉴于当今核武器的解密,因此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把记忆用文字留下来。
那是1976年5月的一个夜晚,一个严肃而神秘的营以上及有关连干部会议在团作战室召开。团长薛幻堂一脸严肃地宣布:上级命令我们团机关带上作战通讯参加罗布泊“7601”核演习,也就是说我们要参加我军首次在原子弹实爆条件下的实兵演习。虽然我们知道当兵就意味着牺牲这些大道理,但听到这个命令后,现场的空气顿时凝固了。虽然我们平时都喊原子弹是纸老虎,但当原子弹真的要在我们面前爆炸时,我想对每一个生命都是一场彻骨的震撼。原子弹就是原子弹,它不同于常规武器。意志和生命在原子弹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更何况是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没有任何保险,再加上当时的投弹方式落后,只能用飞机投掷,万一理论和实际投掷间出现任何偏差和失误,后果将不堪设想。
会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团长后来讲了些什么,在我的脑海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只记得参战首长逐个进行了表态发言。为了不把恐惧情绪带给战士,政委要求我们迅速调整心态,以战争的精神状态对待这次演习,要做到内紧外松。我们这些带兵的人很快就跳出了恐惧的包围圈,组织全体参战官兵做好各项准备,层层进行了动员教育,开展了各种表决心挑应战活动。但是神秘感和恐惧感始终在参战人员中悄悄地蔓延,有的战士把自己省吃俭用的津贴费寄回了家,有的把自己的衣服包裹托付给了留守人员,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味道。
当时我在通讯连任指导员。1976年6月初,我随机关带领通讯连电台、报话班、架设排、通讯排开进了神秘的原子弹实验基地—罗布泊。当时我们从库车营房出发,经过库尔勒到达和硕县乌什塔拉的马兰。在公路左侧的不远处是巍巍的天山,有一条路通往天山脚下马兰机关基地。马兰基地是1959年组建的核试验核爆领导机构,那里本是没有人烟的天山谷地,因遍地开满了马兰花,随被命名为马兰基地。在公路的另一侧则是一望无边的大戈壁滩,路边有一个岔路口,没有任何标志,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岔路口,如果不知底细,谁也不会知道这条土路是干什么用的。这就是通往罗布泊核爆试验场的路,这是一条撑起中国脊梁的了不起的路!车队拐过路口,转向东南方向行驶最初一段路,路边还有一些草,后来连一根草也没有了,尽是茫茫戈壁,汽车跑了200多公里进入了罗布泊。我们住的是通讯连的一个住地,没有核任务时,人员都撤离了。房屋的下半部却是在地面以下,而且窗户都特别小。开始我们不明白房子为什么要建成这样?后来知道了,这样的房屋构造,在罗布泊特殊的核试验环境中,防风保暖,防暑防爆,当初设计建设的人真是苦心有为啊!
开始前两天,基本上是了解当地的地形地物情况,那一片区域,曾经多次核爆炸,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黑色和白色两种颜色,除了茫茫的戈壁滩,就是被原子弹爆炸烧焦的沙砾。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就在这里,爆心地面有一个直径180米的圆坑。坑旁边趴着扭曲的蛇形钢架,这就是中国震惊世界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遗迹。那时不懂得还有没有辐射残留,在坑旁边逗留了十几分钟才离开,那片区域里有试验核爆威力的各种建筑物,还有飞机、军舰等各种武器,有的建筑物已被摧毁,飞机军舰也扭曲变形。那是一片天上没有飞鸟,地上不长寸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地方,更是见不到一滴水。我们吃水用水,专门有一个车队从二、三百公里外的马兰基地运过来的,拉水的费用比汽油费还贵。首长要求我们节约用水,大家洗漱洗衣服都很节约。
艰苦的三个月强化训练从此开始了,我们的第一节课是基地的一位40多岁的女工程师讲原子弹的4大杀伤威力--早期核辐射、光辐射、冲击波和放射性沾染。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们才真正了解了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在后来的训练中,我们都围绕原子弹的4大杀伤威力开展针对性的训练。时间是最好的良医,恐惧感和神秘感在实践和训练中慢慢淡化了。
演习期间伙食补贴较高,几乎每天都有肉,不过这些肉是国家储存多年的冻肉,吃起来有些哈喇味。一顿好几个菜,但战士根本吃不香,因为这里温度太高,白天沙里几乎能烤熟鸡蛋。春夏之交,天气越来越热,大风也开始发威了,部队进入野外训练阶段,领略了罗布泊荒漠戈壁恶劣气候的艰苦磨练。有一段时间,连续刮了几天大风,正值部队野外训练,疾风一阵阵刮来,沙土遮天蔽日,指头大的石块打的人生疼,人根本站立不住,只得趴在地上。刮风的第一天,中午在野外吃饭,大家像往常一样,用饭碗领饭菜,结果饭菜根本无法下肚,尘土沙粒落在碗里,吃的时候无法咀嚼。第二天依然狂风劲吹,中午开饭时,炊事班想了个办法,炊事员坐在八座北京吉普车里,馒头装在开水保温桶里,菜是罐头肉,吉普车停在背风处,门只开一点缝,每个人领饭时,将双手伸进车里,炊事员将夹好罐头肉的馒头塞到双手中,然后双手捧着馒头背风蹲着吃。即使这样,细小的沙粒依然从指缝中钻到馒头上,到了嘴里,上下牙还是不能合咬咀嚼。我的办法是,不咬到底,囫囵吞枣。我们连住的全是帐篷,连续的狂风,刮倒吹跑了许多帐篷,倒了再搭,搭了又被吹倒,风沙吹到帐篷里,睡觉都是蒙着头睡。
进入伏天,风刮的少了,戈壁滩的炎热酷暑却来了,参演部队的训练也进入了关键时刻。戈壁滩上,烈日炎炎下,地表温度达到70多度,开始还能感到烘烤的热浪,不长时间就热得麻木了,感觉不到热的难以忍受了。但整个身体机能却迅速下降,反应迟钝,行动缓慢,身体内的水分很快就挥发殆尽。虽然人不停地出汗,却看不见汗珠,每个人的衣服上没有湿的汗渍,只有一片片汗水蒸发后留下的白色的盐迹。我们通讯连架线排拔杆架线,徒步放线一天喝了十六大锅开水。通讯排顶着烈日,戴着防毒面具往返奔跑,由于太阳的灼烤,有的战士摘下面具,紧贴面具的脸皮都被撕了下来。徒步通讯班一个项目训练完毕,脱下防护服,汗水就像水桶倒水一样流出来。每个人的体重平均减少了十斤左右,大家都盼着早日结束演习,快点离开这个神秘又危险的地方。
核爆炸的日子定于9月9日,可是9月9日却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的消息,泪水顿时像倾盆大雨,各种追悼会成了头等大事,演习自然被推迟了。9月16日这个恐惧而期盼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5日下午,总参李达副总长,乌鲁木齐军区杨勇司令员,郭林祥政委以及各大军区、各兵种首长都来到了场区罗布泊。9月16日那天,天气异常晴朗,部队在8点钟以前做好了一切准备,10点钟准时进入到距爆心11公里的阵地。11点钟,所有的参演战士全部穿上了防护服,戴上了手套,脖子上绑上了白毛巾,戴上1000倍防护眼镜,等待神圣时刻的到来。随着飞机在我们上空盘旋,我们每个人都在心中祈祷,飞机千万不要偏离了爆心,一定要投准。因为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偏差,后果都会不堪设想。飞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了3圈以后,高音喇叭传来了倒计时的声音。12点整,一声起爆令下,一个白色的火球在距地面200米的空中腾空而起,一道刺眼的白炽光芒一闪,继而一团火球崩裂下来撕碎了长空的爆炸声,使所有在场人的身体一抖,震撼心肺。那光极白,那声音极脆极烈,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到过。巨大的蘑菇云翻腾升空,一股灼热感迅速袭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鼓满耳膜,巨大的冲击波随之席卷而来,平日里死寂般的戈壁滩如飓风突至,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后来才听说,这次核爆的原子弹设计当量是3万吨,实爆时达到了3.9万吨的上限。
半小时后,冲锋号吹响了。参演部队、坦克、装甲车、大炮和各种车辆以宏大的阵势浩浩荡荡地向爆心开进。军人的职责使我们暂时忘掉了恐惧,按照训练计划,落实了各种战术动作,消灭了入侵的贝尔戈兰敌军,顺利完成了战斗任务。冲锋中涌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死亡和沉寂,从外到内,房屋设施从依然矗立到残垣断壁,再到夷为平地。昨天刚刚放置的狗、猴子等实验动物,在光辐射、冲击波的作用下,瞬间变成了焦尸。飞机散了架,各种汽车都认不出模样,各式大炮都变成了油条麻花,连战场上的苏式老大坦克都被掀掉了炮塔。爆心地区的地表土层被爆炸出40公分左右的虚土,表面的土石则被核爆的高温烧得像一层炼钢炉渣。这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地狱,什么是死亡。经过一个多小时艰难跋涉,终于走出了死亡之海。接着部队开往洗消站,进行冲洗和测量,在确保辐射剂量不对生命形成威胁的情况下,部队撤出爆区。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才真正明白,死亡被我们暂时甩在了身后,绷了3个月的心终于放松了。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始终刻在我的脑海里。罗布泊,这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却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罗布泊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它伴随我走过了许许多多的路,爬过了许许多多的山,它给了我坚强,给了我信念,它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使我受益终生。我感谢这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