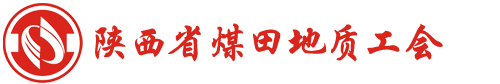好家风,无言的教诲
某次神州系飞船发射成功的庆功宴上,一位老航天人豪言壮阔:“为了祖国献青春,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当时,坐在电视机前的我深有感触:我们地质人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说起来,我们家并不能算是根正苗红的地质世家--除了父亲是专业的地质工作者。但是我们祖孙三代却都绕不开一个关键的词---地质人,爷爷用他最心爱的算盘将父亲送入地质行业,而我是一三一公司机关部门里的一名普通科员。虽有些牵强,但也算是事实。
爷爷的算盘
我见过爷爷的算盘:那是一个用木头做的长方形的算盘,边框已经有些松动,一共有13串珠子,中间用木头隔开,长久的使用让珠子磨的有些发光。说起这个算盘,也是有点故事的。
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爷爷奶奶经人介绍结婚,婚后生育了六个孩子。家里由于孩子较多,条件一直不好,父亲没有好衣服穿,还吃不饱肚子,但是父亲学习很刻苦,肯下功夫,老在班里拿第一名。
为了养家糊口,奶奶就在家干农活,爷爷出门贩卖东西,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这把老算盘。据父亲说当时因为爷爷会用算盘,干活效率高,能在外面挣钱,所以他能一直上到大学,这一度成为父亲炫耀的资本。爷爷在世的时候经常说“把算盘收好,算盘在就有饭吃。”
爷爷常说“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爷爷确实是出了名的认真,干活也利索。就这样,靠着一把算盘,爷爷将爸爸送入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爷爷执意让父亲选择了地质行业。当年我爷爷内心里,有着一种“以艰苦奋斗为荣”的信念,心想父亲既然读了大学,就要为国家效力。就这样,一个最最朴素的出发点,掀开了我家历史的新一页。从此父亲多了一个新的身份:地质人。
爸爸的地质三宝
我爸跟我爷爷有一个共同的神奇的本领---认真。
大学毕业后的我爸,服从学校分配,背着他的“地质三宝”来到了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陕西省一三一煤田地质有限公司。据说临上班前几天,我奶奶天天抹眼泪。她知道儿子这一走,可不是去坐办公室喝茶看报,而是漫山遍野的挖矿找煤。可爷爷说:“要干地质这一行,就是要吃苦!”就这样,还很瘦弱的老爸,背着铺盖,来到了韩城,拿起了地质锤,开始了他的地质生涯。
从1984年进入单位到现在,34年的时间里,光是他驻扎超过半年的县市,就不下十余个,足迹遍布全陕西省,靠着他那股认真的劲儿,从一个稚嫩的鉴定员,成长为一个独当一面的项目带头人,带着队伍每年创造出不斐的业绩,获得各种荣誉。其中的辛苦,我无法说出“感同身受”这样的漂亮话,毕竟野外工作我只体验过短短的一年。
2007年,爷爷病重,老爸工作任务较重,回家陪爷爷的时间少之又少,就连爷爷过世的时候他也是当天才赶回家的,好长一段时间,我都理解不了父亲,觉得他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
渐渐的我才知道,这样的情况,在地质系统很常见,好多地质人因为工作两地分居,半年甚至更长时间都见不到家人。他们这群人,真的有着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一切疲劳与寒冷的热情,克服这世界上所有艰难困苦的热情。
我的地质梦
其实,毕业之前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也会成为一名地质人。临近毕业,爸爸表态希望我进入地质单位,父女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我的立场功利而自我:作为一个与地质丝毫不沾边的理科生,进入地质系统缺乏施展空间,只能从事财务统计等的边缘性岗位;行业收入虽然稳定但是并不优渥;社交圈过于狭窄,生活可能就此陷入一成不变的沉闷。
我爸的观点诚恳却犀利:地质行业虽说艰苦,但确实能锻炼一个人,而且地质行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化发展已经具备了合理的体系结构,理科生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再加上后期一些培训教育,前景还是有的。真正老旧刻板的不是地质行业,根本就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份工作的我自己。
最后爸爸说:“我对地质工作是有感情的,希望你能够来试试。”
2012年,我进入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科员。在初进单位一年的野外实习中,学会了很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面对着以前同学“你怎么去了这种单位”的质疑,我选择了属于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这是另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因此我在工作的这几年里认真学习做各种工程预算、编写标书,以一名地质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想这是我作为一名准地质人唯一可以为地质事业贡献的微薄力量。
好的家风,无需过多的言语。家风家训传承到我这一代已经变成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认真”。生于地质人家庭,感受地质人家风,父辈们在工作中的认真态度和为地质奉献的精神,老地质人的情怀和担当不仅仅是我更是我们年轻一代地质人应该学习和传承的。这种精神时时督促着我们,让我们在彷徨时当机立断,在失落时振奋精神,在身处逆境时披荆斩棘,所向披靡。
编者:该文荣获陕西省能源化学地质系统2018年“书香三八”读书活动征文类三等奖。